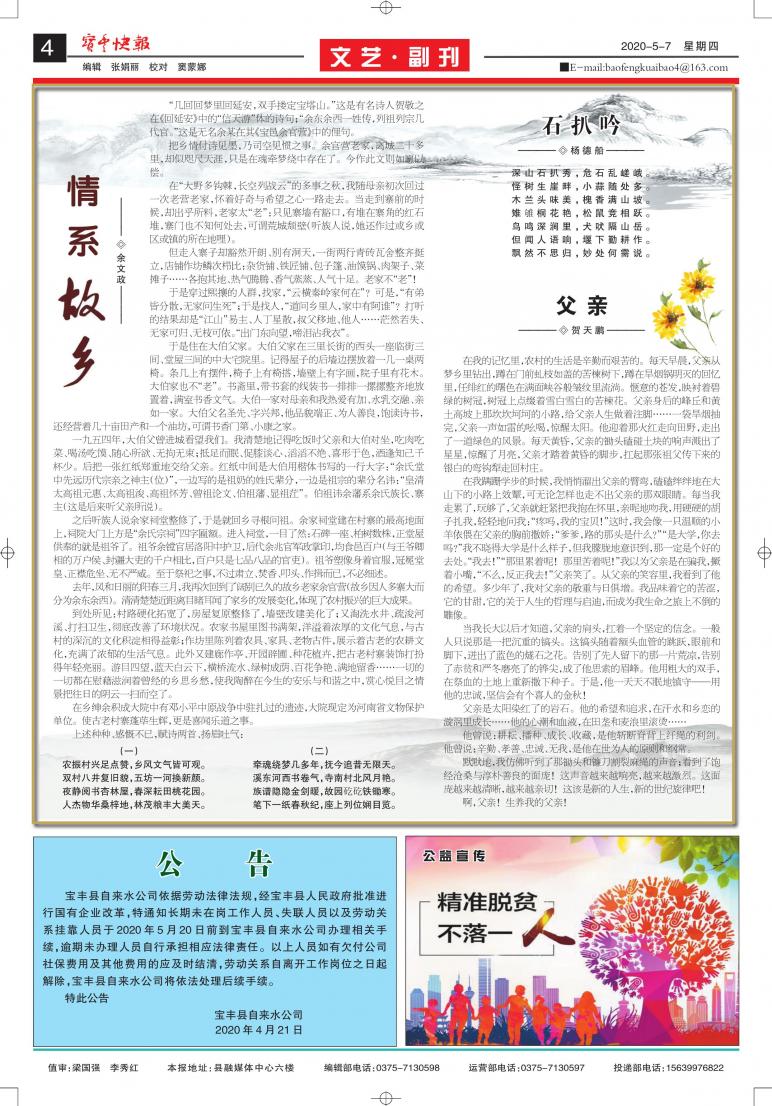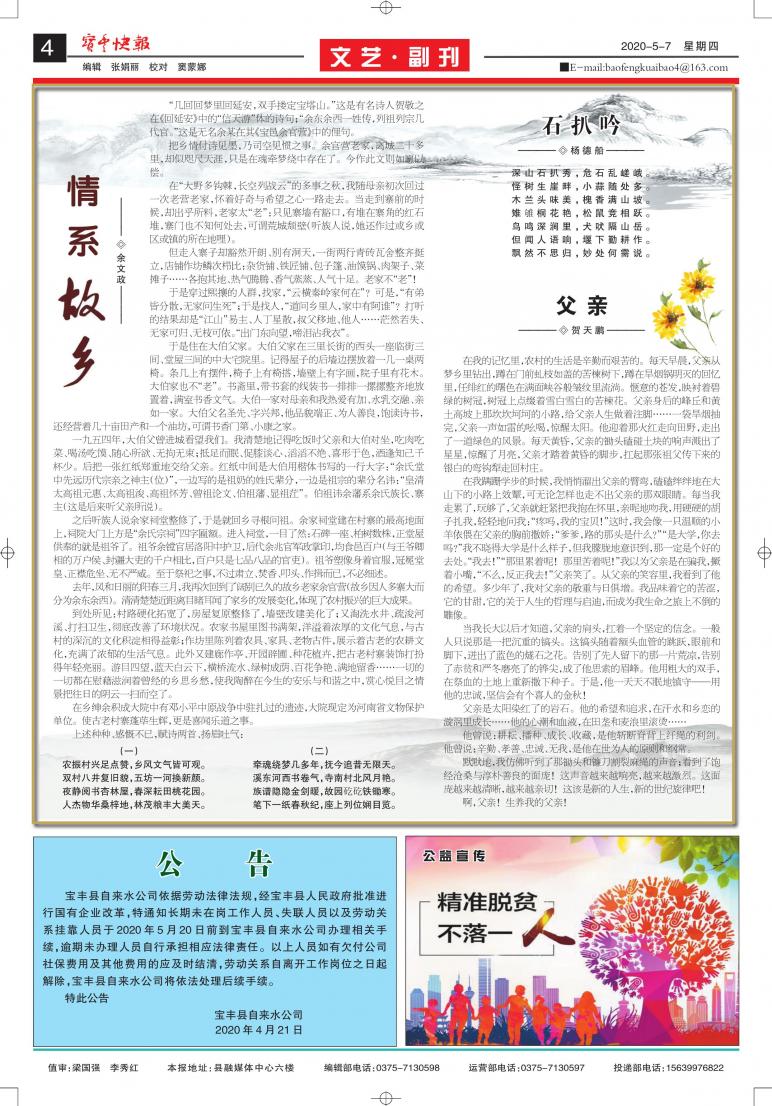
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,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这是有名诗人贺敬之在《回延安》中的“信天游”体的诗句;“余东余西一姓传,列祖列宗几代官。”这是无名余某在其《宝邑余官营》中的俚句。
把乡情付诗见墨,乃司空见惯之事。余官营老家,离城二十多里,却似咫尺天涯,只是在魂牵梦绕中存在了。今作此文则如愿以偿。
在“大野多钩棘,长空列战云”的多事之秋,我随母亲初次回过一次老营老家,怀着好奇与希望之心一路走去。当走到寨前的时候,却出乎所料,老家太“老”:只见寨墙有豁口,有堆在寨角的红石堆,寨门也不知何处去,可谓荒城颓壁(听族人说,她还作过或乡或区或镇的所在地哩)。
但走入寨子却豁然开朗、别有洞天,一街两行青砖瓦舍整齐挺立,店铺作坊鳞次栉比:杂货铺、铁匠铺、包子篷、油馍锅、肉架子、菜摊子……各抱其地、热气腾腾、香气蒸蒸、人气十足。老家不“老”!
于是穿过熙攘的人群,找家,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?可是,“有弟皆分散,无家问生死”;于是找人,“道问乡里人,家中有阿谁”?打听的结果却是“江山”易主、人丁星散,叔父移地、他人……茫然若失、无家可归、无枝可依。“出门东向望,啼泪沾我衣”。
于是住在大伯父家。大伯父家在三里长街的西头一座临街三间、堂屋三间的中大宅院里。记得屋子的后墙边摆放着一几一桌两椅。条几上有摆件,椅子上有椅搭,墙壁上有字画,院子里有花木。大伯家也不“老”。书斋里,带书套的线装书一排排一摞摞整齐地放置着,满室书香文气。大伯一家对母亲和我热爱有加、水乳交融、亲如一家。大伯父名圣先、字兴邦,他品貌端正、为人善良,饱读诗书,还经营着几十亩田产和一个油坊,可谓书香门第、小康之家。
一九五四年,大伯父曾进城看望我们。我清楚地记得吃饭时父亲和大伯对坐,吃肉吃菜、喝汤吃馍、随心所欲、无拘无束;抵足而眠、促膝谈心、滔滔不绝、喜形于色,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后把一张红纸郑重地交给父亲。红纸中间是大伯用楷体书写的一行大字:“余氏堂中先远历代宗亲之神主(位)”,一边写的是祖奶的姓氏辈分,一边是祖宗的辈分名讳:“皇清太高祖元惠、太高祖浚、高祖怀芳、曾祖论文、伯祖藩、显祖茳”。伯祖讳余藩系余氏族长、寨主(这是后来听父亲所说)。
之后听族人说余家祠堂整修了,于是就回乡寻根问祖。余家祠堂建在村寨的最高地面上,祠院大门上方是“余氏宗祠”四字匾额。进入祠堂,一目了然:石碑一座、柏树数株,正堂屋供奉的就是祖爷了。祖爷余镗官居洛阳中护卫,后代余兆官军政掌印,均食邑百户(与王爷卿相的万户侯、封疆大吏的千户相比,百户只是七品八品的官吏)。祖爷塑像身着官服,冠冕堂皇、正襟危坐、无不严威。至于祭祀之事,不过肃立、焚香、叩头、作揖而已,不必细述。
去年,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,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老家余官营(故乡因人多寨大而分为余东余西)。清清楚楚近距离目睹耳闻了家乡的发展变化,体现了农村振兴的巨大成果。
到处所见:村路硬化拓宽了,房屋复原整修了,墙壁改建美化了;又淘洗水井、疏浚河溪、打扫卫生,彻底改善了环境状况。农家书屋里图书满架,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,与古村的深沉的文化积淀相得益彰;作坊里陈列着农具、家具、老物古件,展示着古老的农耕文化,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此外又建廊作亭、开园辟圃、种花植卉,把古老村寨装饰打扮得年轻亮丽。游目四望,蓝天白云下,横桥流水、绿树成荫、百花争艳、满地留香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在慰藉滋润着曾经的乡思乡愁,使我陶醉在今生的安乐与和谐之中,赏心悦目之情景把往日的阴云一扫而空了。
在乡绅余积成大院中有邓小平中原战争中驻扎过的遗迹,大院现定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使古老村寨蓬荜生辉,更是喜闻乐道之事。
上述种种、感慨不已,赋诗两首、扬眉吐气:
(一)
农振村兴足点赞,乡风文气皆可观。
双村八井复旧貌,五坊一河换新颜。
夜静阅书杏林屋,春深耘田桃花园。
人杰物华桑梓地,林茂粮丰大美天。
(二)
牵魂绕梦几多年,抚今追昔无限天。
溪东河西书卷气,寺南村北风月艳。
族谱隐隐金剑暖,故园矻矻铁锄寒。
笔下一纸春秋纪,座上列位娴目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