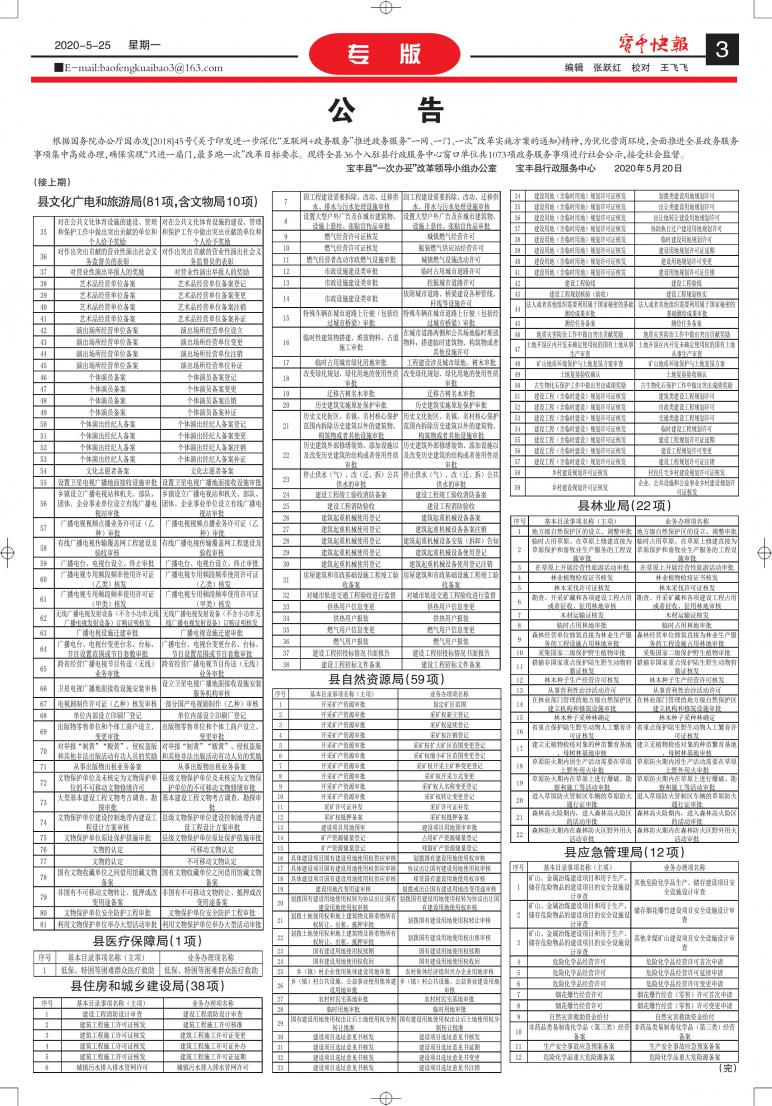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
“歌咏言、诗言志”,诗可以颂、可以讽……乃老生常谈。我于此文中标新立异,谈谈诗的魅力。
小时候,父亲教我写字,父亲写的仿影中有“草铺橫野六七里,笛弄晚风三四声……”书体、诗意、熏陶、感荡、启蒙着我稚幼的心灵,至今仍历历在目,不失不忘。
中三时,司连辰老师语文课上念了“范文”,文中有我的一首顺口溜:“山连山水漫漫,树连树花艳艳……”也许是因为“诗”的“魅力”,老师弃文而谈“诗”了。至今想起来,不无汗颜。
中学几年中,读了十多本长篇小说:《三家巷》、《三里湾》……有幸从《子夜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中读到了诗歌,如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,今宵离别后,何日君再来……”如获至宝,如古玩摊上见了汝瓷,渤海边上捡了美石,九分惬意。
接着,我读到了《诗刊》、《京剧丛刊》,牛进了菜园,人漫游诗海,饥而饭,蜂见蜜,尽情吮吸诗的乳液,以致骨软筋麻,如痴如醉。诗的魅力像苏轼水边醉卧醒来,见山拥水响,疑非尘世一样,以致感到人活着是如此之美妙了。
明代文学家、剧作家、诗书画家徐文长,把他在文化上的建树排了一下次序,我也想把自己的爱好排排次序,但不能和徐渭相提并论、等量齐观,若一定要以小比大,诗排首位。
有道是“文备诸体”(古典小说中诗词多多),文中有诗、画中有诗、书法有诗。诗的魅力像磁石似的把我紧紧地吸引了。
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我在漯高上学。校方号召我们大力写作歌颂时代精神的诗歌,正中下怀。于是胡论瞎侃、援笔立就。依稀记得一首:“跃进歌声多又多,跃进歌声用马驮。前马刚到宝丰县,后马已过二郎河”。自鸣得意,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“合格产品”,不知羞笑为何物,但却是生活的增补剂、精神的调味品了。
后来,我读了四大名著。一经谋面就爱不释卷。书的回目是诗句、褒贬人物是诗句,写景状物也是诗句。特别是《红楼梦》,第一回中就先声夺人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!”令人感撼而悲怆。诗社中更是好诗如珠、佳作跌出、风格纷呈,令人目不暇接。在诗境中流连、在诗海中泛舟,魅力袭心,不同的诗作,让人回肠荡气,撕心裂肺;让人如沐春风,如嚼甘饴;让人怡然自得,让人潸然泪下;让人如离尘而归去、凌风而登仙……也如久旱逢甘霖、炎夏抱了“竹夫人”(而非贴了王道士的狗皮膏、吃了胡庸医的虎狼药)。满汉全席的精神盛宴让人成了饕餮之辈。
至于满架图书中,唐宋等诗词选本成了必读之书,成了生活的密友。“滴荷花露写唐诗”,也成了效颦之举了。
一九六零年假期,我与王庭文先生(字魁甫)在几个单位写字作画。王老师在他画的《梅花迎春》图中题了一首自作诗,记得其中两句是:“鸟得枝栖声声唱,花逢雪飞朵朵新。”颇令我为之倾倒。题画诗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老师的崇敬之情。
至于在此后的文化沙漠中与诗友酬答、赠答,让诗的魅力化为血浆,让精神变为物质而乐此不疲。
诗的魅力何止于此。趣味多多,再略举几例吧。
唐安史之乱使王维陷敌而就伪职,令人诟病。但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的美佳之作且五律尤为唐诗之最的他,仍颇为后人推崇,岂非因为诗的魅力?
现代医科大师屠呦呦,因为喜爱曹操《短歌行》中的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”而得此名。曹曾误杀华佗,她的这位同行,并未让大师引以为恨反而化“敌”为友,化干戈为玉帛,岂不是诗的魅力、建安文学之魅力所致吗?
国外有诗歌医院(欧洲有、日本也有),不多问诊也不施药,只送不少诗歌书籍,海涅、泰戈尔的,普希金、马雅可夫斯基的……让患者拿去经常诵读,让诗的魅力使人乐而忘病,精神疗法让人心旷神怡、心广体胖,据说还真有些疗效哩。
清代诗人、书画大家郑板桥孤卧江村时节,一天深夜,月色淡淡、风声萧萧,忽听窗外响动,隔窗向外一觑,只见一人越墙而过,手持短刀、蹑手蹑脚向房门逼近。这情况谁见了不毛骨悚然?而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学究,此时此刻该如何应对呢?只好坐以待偷、破财免灾了?非也。壮士见辱、拔剑而起!无剑可拔。那就操起砚台砸他龟儿。也不是。而是平心静气、处险不惊、一阵思索、诗上心来:“大风起兮月色昏,有劳君子到寒门。腹内诗书藏千卷,家中钱串无半根。出院莫惊黄尾犬,越墙别坏绿花盆。夜深不及披衣送,收拾雄心回自村。”
谁知那贼还就洗耳恭听,知羞知趣而出退了。
终是贼人人性不泯,诗的魅力有加,何况还有板桥老先生的修养、智力等等因素,从而成就了一段诗界佳话与文林趣谈。
意犹未尽,聊以拙诗和之于郑公,以结拙文:
无论白昼与黄昏,恭候同仁临篷门。
红花迎宾一朵朵,绿竹招友几根根。
座边不置烟灰碟,案头只放墨水盆。
锦绣山川三万里,移缩庭前看江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