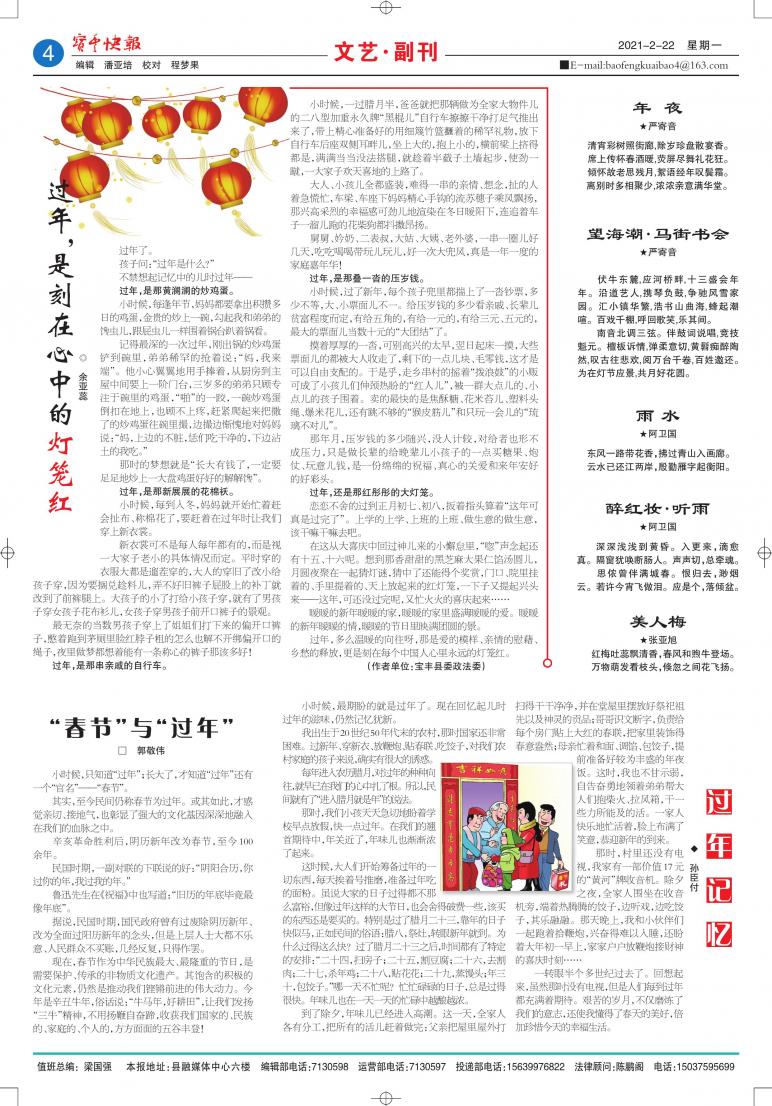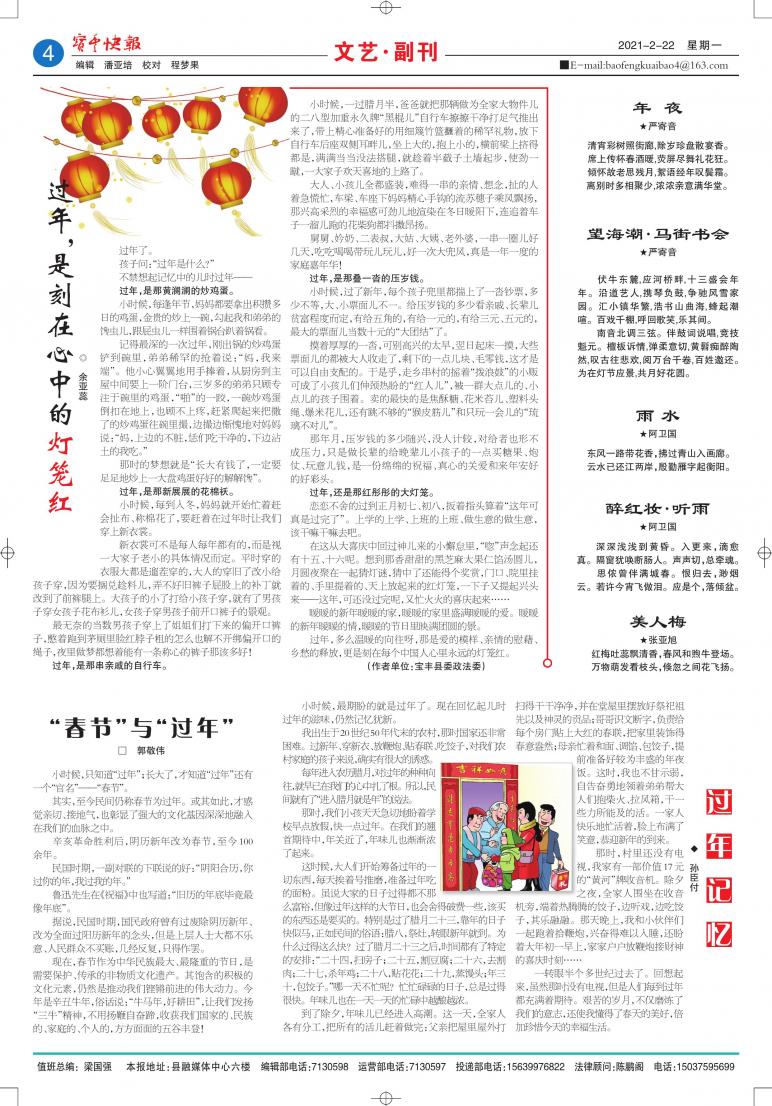
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
过年了。
孩子问:“过年是什么?”
不禁想起记忆中的儿时过年——
过年,是那黄澜澜的炒鸡蛋。
小时候,每逢年节,妈妈都要拿出积攒多日的鸡蛋,金贵的炒上一碗,勾起我和弟弟的馋虫儿,跟屁虫儿一样围着锅台趴着锅看。
记得最深的一次过年,刚出锅的炒鸡蛋铲到碗里,弟弟稀罕的抢着说:“妈,我来端”。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捧着,从厨房到主屋中间要上一阶门台,三岁多的弟弟只顾专注于碗里的鸡蛋,“啪”的一跤,一碗炒鸡蛋倒扣在地上,也顾不上疼,赶紧爬起来把撒了的炒鸡蛋往碗里撮,边撮边惭愧地对妈妈说:“妈,上边的不脏,恁们吃干净的,下边沾土的我吃。”
那时的梦想就是“长大有钱了,一定要足足地炒上一大盘鸡蛋好好的解解馋”。
过年,是那新展展的花棉袄。
小时候,每到入冬,妈妈就开始忙着赶会扯布、称棉花了,要赶着在过年时让我们穿上新衣裳。
新衣裳可不是每人每年都有的,而是视一大家子老小的具体情况而定。平时穿的衣服大都是遛茬穿的,大人的穿旧了改小给孩子穿,因为要搁兑趁料儿,弄不好旧裤子屁股上的补丁就改到了前裤腿上。大孩子的小了打给小孩子穿,就有了男孩子穿女孩子花布衫儿,女孩子穿男孩子前开口裤子的景观。
最无奈的当数男孩子穿上了姐姐们打下来的偏开口裤子,憋着跑到茅厕里脸红脖子粗的怎么也解不开绑偏开口的绳子,夜里做梦都想着能有一条称心的裤子那该多好!
过年,是那串亲戚的自行车。
小时候,一过腊月半,爸爸就把那辆做为全家大物件儿的二八型加重永久牌“黑棍儿”自行车擦擦干净打足气推出来了,带上精心准备好的用细篾竹篮擓着的稀罕礼物,放下自行车后座双侧耳畔儿,坐上大的,抱上小的,横前梁上挤得都是,满满当当没法搭腿,就趁着半截子土墙起步,使劲一蹴,一大家子欢天喜地的上路了。
大人、小孩儿全都盛装,难得一串的亲情、想念,扯的人着急慌忙,车梁、车座下妈妈精心手钩的流苏穗子乘风飘扬,那兴高采烈的幸福感可劲儿地渲染在冬日暖阳下,连追着车子一溜儿跑的花柴狗都抖擞昂扬。
舅舅、妗奶、二表叔,大姑、大姨、老外婆,一串一圈儿好几天,吃吃喝喝带玩儿玩儿,好一次大兜风,真是一年一度的家庭嘉年华!
过年,是那叠一沓的压岁钱。
小时候,过了新年,每个孩子兜里都揣上了一沓钞票,多少不等,大、小票面儿不一。给压岁钱的多少看亲戚、长辈儿贫富程度而定,有给五角的,有给一元的,有给三元、五元的,最大的票面儿当数十元的“大团结”了。
摸着厚厚的一沓,可别高兴的太早,翌日起床一摸,大些票面儿的都被大人收走了,剩下的一点儿块、毛零钱,这才是可以自由支配的。于是乎,走乡串村的摇着“拨浪鼓”的小贩可成了小孩儿们伸颈热盼的“红人儿”,被一群大点儿的、小点儿的孩子围着。卖的最快的是焦酥糖、花米苔儿、塑料头绳、爆米花儿,还有跳不够的“猴皮筋儿”和只玩一会儿的“琉璃不对儿”。
那年月,压岁钱的多少随兴,没人计较,对给者也形不成压力,只是做长辈的给晚辈儿小孩子的一点买糖果、炮仗、玩意儿钱,是一份绵绵的祝福、真心的关爱和来年安好的好彩头。
过年,还是那红彤彤的大灯笼。
恋恋不舍的过到正月初七、初八,扳着指头算着“这年可真是过完了”。上学的上学、上班的上班、做生意的做生意,该干嘛干嘛去吧。
在这从大喜庆中回过神儿来的小懈怠里,“唿”声念起还有十五、十六呢。想到那香甜甜的黑芝麻大果仁馅汤圆儿,月圆夜聚在一起猜灯谜,猜中了还能得个奖赏,门口、院里挂着的、手里提着的、天上放起来的红灯笼,一下子又提起兴头来——这年,可还没过完呢,又忙火火的喜庆起来……
暖暖的新年暖暖的家,暖暖的家里盛满暖暖的爱。暖暖的新年暖暖的情,暖暖的节日里映满团圆的景。
过年,多么温暖的向往呀,那是爱的模样、亲情的慰藉、乡愁的释放,更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里永远的灯笼红。 (作者单位:宝丰县委政法委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