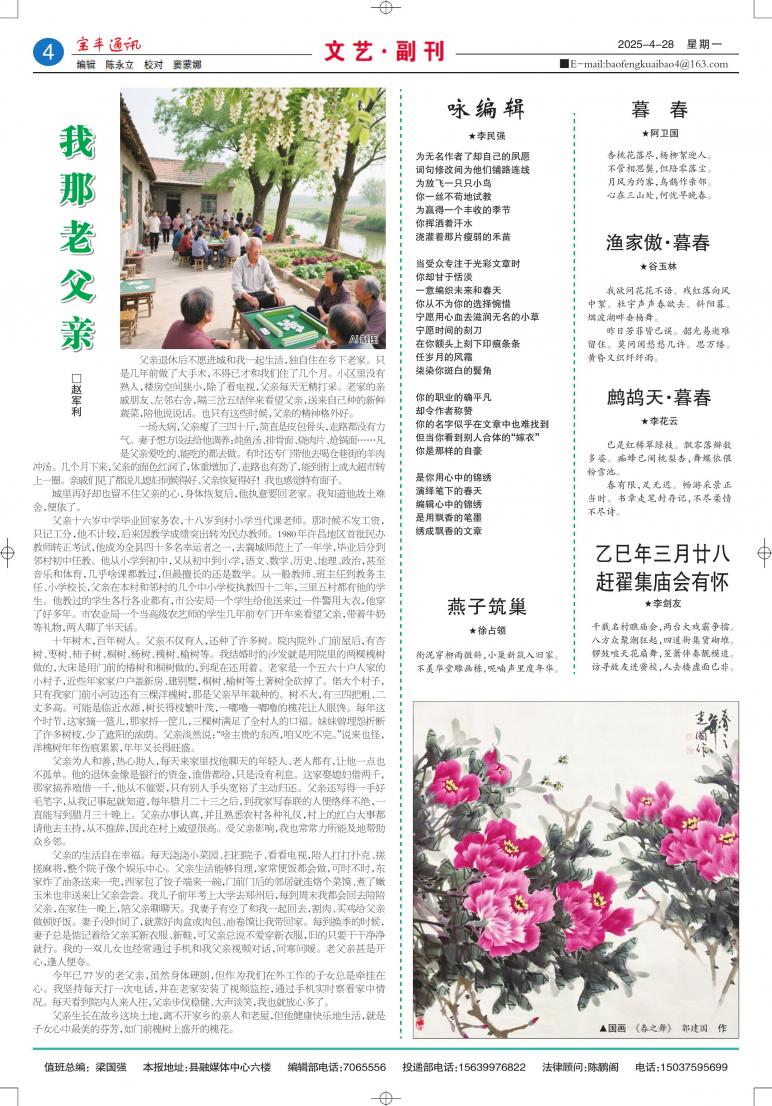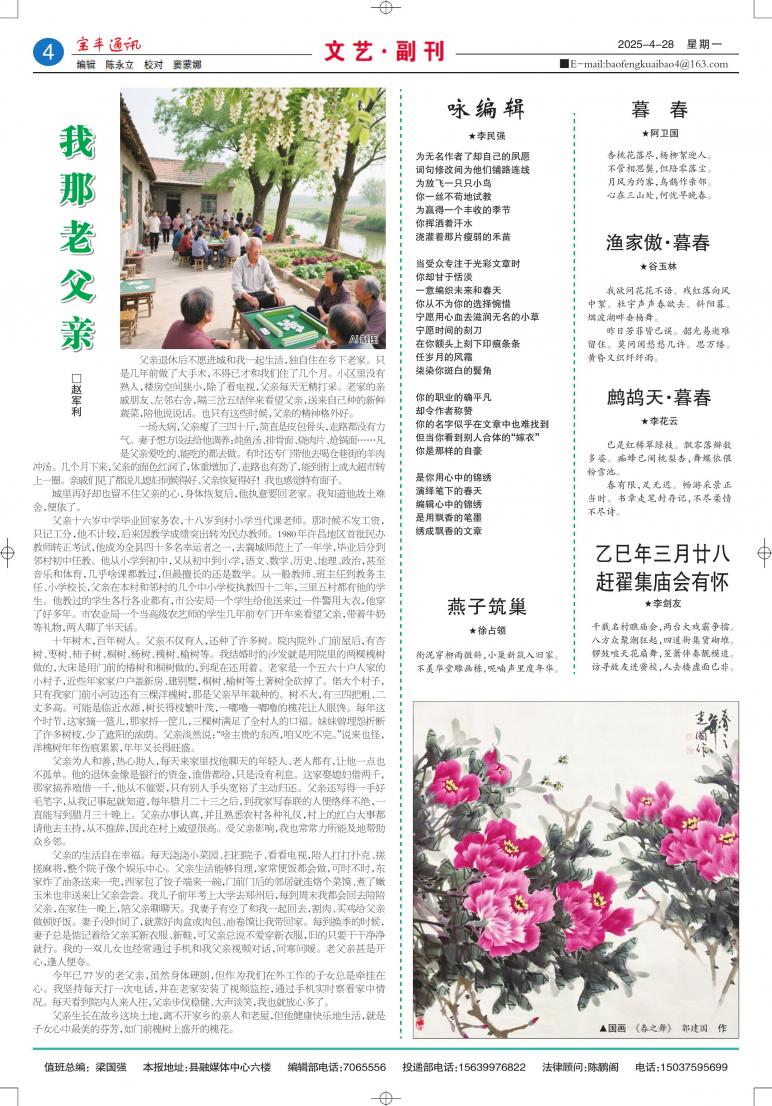
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
父亲退休后不愿进城和我一起生活,独自住在乡下老家。只是几年前做了大手术,不得已才和我们住了几个月。小区里没有熟人,楼房空间狭小,除了看电视,父亲每天无精打采。老家的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隔三岔五结伴来看望父亲,送来自己种的新鲜蔬菜,陪他说说话。也只有这些时候,父亲的精神格外好。
一场大病,父亲瘦了三四十斤,简直是皮包骨头,走路都没有力气。妻子想方设法给他调养:炖鱼汤、排骨面、烧肉片、炝锅面……凡是父亲爱吃的、能吃的都去做。有时还专门带他去喝仓巷街的羊肉冲汤。几个月下来,父亲的面色红润了,体重增加了,走路也有劲了,能到街上或大超市转上一圈。亲戚们见了都说儿媳妇伺候得好、父亲恢复得好!我也感觉特有面子。
城里再好却也留不住父亲的心,身体恢复后,他执意要回老家。我知道他故土难舍,便依了。
父亲十六岁中学毕业回家务农,十八岁到村小学当代课老师。那时候不发工资,只记工分,他不计较,后来因教学成绩突出转为民办教师。1980年许昌地区首批民办教师转正考试,他成为全县四十多名幸运者之一,去襄城师范上了一年学,毕业后分到邻村初中任教。他从小学到初中,又从初中到小学,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,甚至音乐和体育,几乎啥课都教过,但最擅长的还是数学。从一般教师、班主任到教务主任、小学校长,父亲在本村和邻村的几个中小学校执教四十二年,三里五村都有他的学生。他教过的学生各行各业都有,市公安局一个学生给他送来过一件警用大衣,他穿了好多年。市农业局一个当高级农艺师的学生几年前专门开车来看望父亲,带着牛奶等礼物,两人聊了半天话。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父亲不仅育人,还种了许多树。院内院外、门前屋后,有杏树、枣树、柿子树、桐树、杨树、槐树、榆树等。我结婚时的沙发就是用院里的两棵槐树做的,大床是用门前的椿树和桐树做的,到现在还用着。老家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,近些年家家户户盖新房、建别墅,桐树、榆树等土著树全砍掉了。偌大个村子,只有我家门前小河边还有三棵洋槐树,那是父亲早年栽种的。树不大,有三四把粗、二丈多高。可能是临近水源,树长得枝繁叶茂,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让人眼馋。每年这个时节,这家摘一篮儿,那家捋一筐儿,三棵树满足了全村人的口福。妹妹曾埋怨折断了许多树枝,少了遮阳的浓荫。父亲淡然说:“啥主贵的东西,咱又吃不完。”说来也怪,洋槐树年年伤痕累累,年年又长得旺盛。
父亲为人和善,热心助人,每天来家里找他聊天的年轻人、老人都有,让他一点也不孤单。他的退休金像是银行的资金,谁借都给,只是没有利息。这家娶媳妇借两千,那家搞养殖借一千,他从不催要,只有别人手头宽裕了主动归还。父亲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从我记事起就知道,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后,到我家写春联的人便络绎不绝,一直能写到腊月三十晚上。父亲办事认真,并且熟悉农村各种礼仪,村上的红白大事都请他去主持,从不推辞,因此在村上威望很高。受父亲影响,我也常常力所能及地帮助众乡邻。
父亲的生活自在幸福。每天浇浇小菜园、扫扫院子、看看电视,陪人打打扑克、搓搓麻将,整个院子像个娱乐中心。父亲生活能够自理,家常便饭都会做,可时不时,东家炸了油条送来一兜,西家包了饺子端来一碗,门前门后的邻居就连烙个菜馍、煮了嫩玉米也非送来让父亲尝尝。我儿子前年考上大学去郑州后,每到周末我都会回去陪陪父亲,在家住一晚上,陪父亲聊聊天。我妻子有空了和我一起回去,割肉、买鸡给父亲做顿好饭。妻子没时间了,就蒸好肉盒或肉包、油卷馍让我带回家。每到换季的时候,妻子总是惦记着给父亲买新衣服、新鞋,可父亲总说不爱穿新衣服,旧的只要干干净净就行。我的一双儿女也经常通过手机和我父亲视频对话,问寒问暖。老父亲甚是开心,逢人便夸。
今年已77岁的老父亲,虽然身体硬朗,但作为我们在外工作的子女总是牵挂在心。我坚持每天打一次电话,并在老家安装了视频监控,通过手机实时察看家中情况。每天看到院内人来人往,父亲步伐稳健、大声谈笑,我也就放心多了。
父亲生长在故乡这块土地,离不开家乡的亲人和老屋,但他健康快乐地生活,就是子女心中最美的芬芳,如门前槐树上盛开的槐花。 (赵军利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