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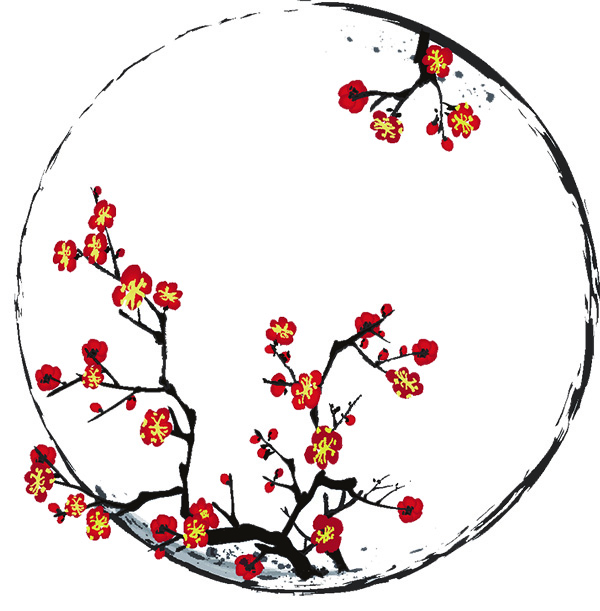
也算是家中的司务兼采购,步履蹒跚地出入大街小巷、不免东张西望,最入眼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壁画,也是这些壁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老旧小区改造、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。于是想起与此壁画有关的“城南旧事”,免不了让记忆的野马在人生的历史大野的广阔天地里脱缰一驰。
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吧,幼时从父学书,接着无师自通学画,先是对着小画片儿画,后来照着书中插图临,有点像鲁迅先生在“三味书屋”时对着《水浒》中的绣像插图描摹的样子和情形。虽是初学乍练,但画来画去,倒也画的安鼻子带眼,有模有样了。有了这点“本钱”,上小学后,在老师的支持下还办了两次小画刊、小文刊哩。
上中学时,老调重弹、重操故技,在我县完中校园里,在班干部和老师的支持下,搞画刊、文刊,红杏出墙,中学独步,无不得意,少不了回家“鬼炸”(炫耀)一番,使得母亲、姐姐还到学校观看了小半天。
在以后漫长而坎坷的岁月里,不管在城、在乡、在校、在机关,不知又经历了多少花开花谢、日上日下,又是怎样的沉浮上下、摸爬滚打,怎样的悲欢离合、苦甜酸辣,怎样的浓淡干湿、点厾挥洒,怎样的劈波斩浪、彩墨生涯。就让事实说话、作品当家。
举俩简例吧。漯高假期,我在城关南后街的农村大食堂的西墙上曾画了巨幅水粉壁画:《劳动者要做文化的主人》。画面上真人大小的工农兵站在一本大书上,光彩夺目,神采奕奕,又给大门题写了“大食堂”匾额三字。也算过了书瘾、画癖,酣畅淋漓。
七十年代上世纪,应丁成功之邀,在杨庄火车站上刷标语。正值赤日炎炎、骄阳似火,梯上作业,高处不胜热;背心湿透,干脆赤膊;一把刷子,几行汗渍;羞颜升天,斯文扫地。坐师政委的吉普车来去,算是逢场作戏,也算猎奇得趣。
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,一观镜中华发,油然而生叹息:朝朝暮暮、矻矻戚戚,不知挥洒了多少彩纸墨迹:滴汗水浇灌土地,绞脑汁作文赋诗,蘸风雨画山画人,乘兴致画竹画菊……从县府大院到山乡僻地,从玉宇厅室到土墙颓壁,写招牌、画板壁、办特刊、刷标语……应邀参与各个展览、各种活动、各次会议,虽衣宽而不悔,且乐此而不疲。“闲来写就青山卖”,自我陶醉心扉开:几顿饭菜几文铜,知足常乐不嫌穷。桂冠乌纱乌(无)问鼎,有子无官一身轻。
我并非执迷不悟、冥顽不化者,于是学学样子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足不出县,让作品“升天”:平顶山六个单位举办“书法篆刻联展”,不但入选了我的书、印作品,还颁发了证书、奖金。井蛙崭露头角,地黄瓜上了“高架”。非是刻意炒作,更不是桂冠争夺,就算是小试“牛刀”吧。
在木札岭避暑时,在山前广场上与市里的陈常山君(退休的领导干部)对着郑、汴、洛、平等地的游客作了多次书法表演;又对着话筒不顾老态龙钟、声嘶力竭、引吭高歌了影视名歌、京剧名段;老有所欢,找回了少年作画的昨天,又酣畅淋漓了一番。这正是:
七律·彩墨人生
鬓白发皤忆岁昨,笔中汗渍笔外歌。
抒情敷彩蕴苍莽,状景泼墨现巍峨。
桂冠半取几束手,费纸百弃一赤膊。
绿园青窗小楼坐,无负日月无蹉跎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