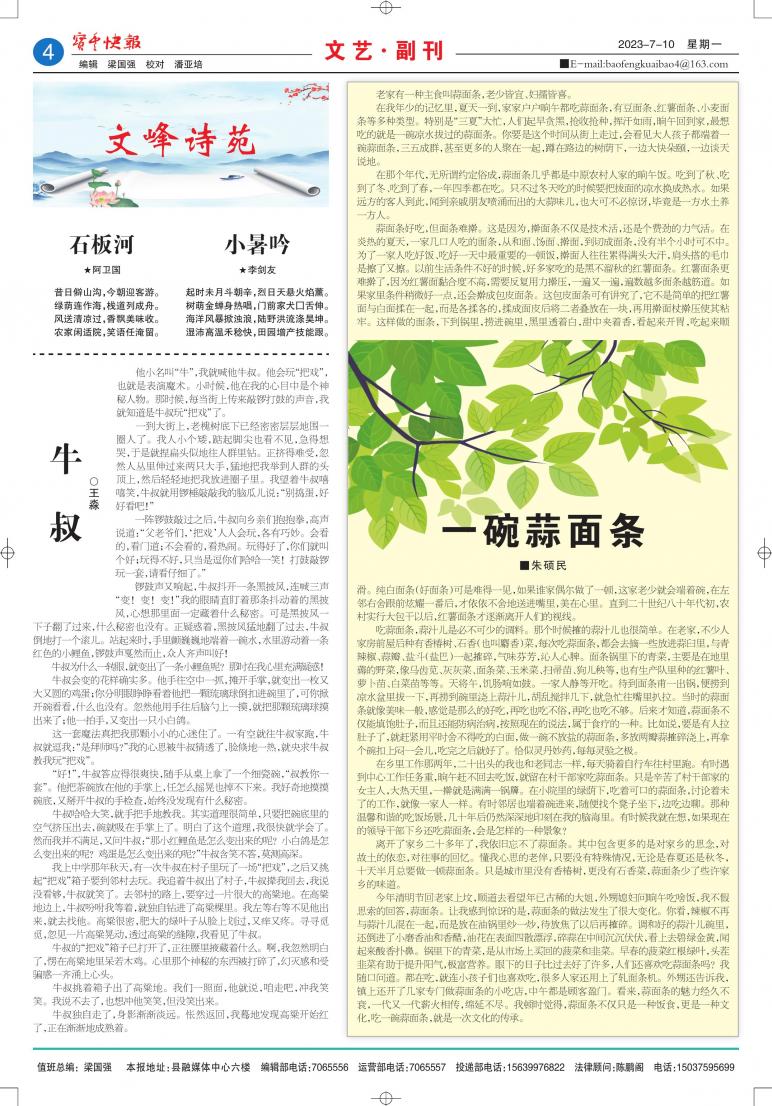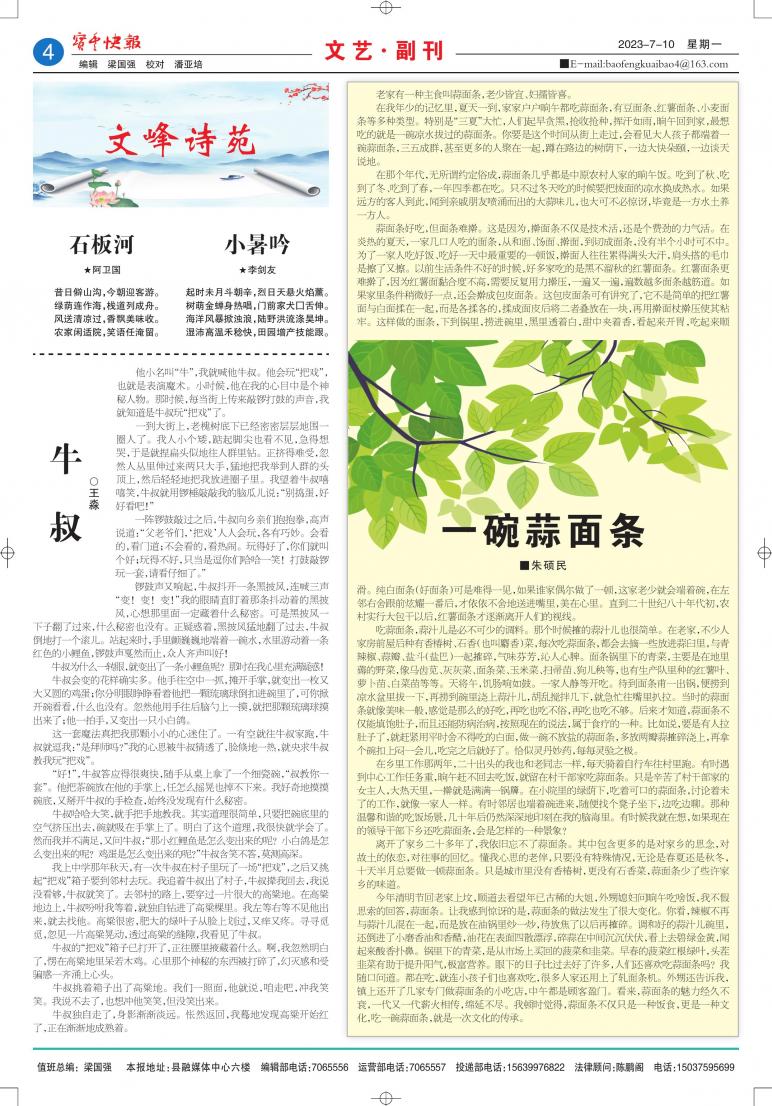
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老家有一种主食叫蒜面条,老少皆宜、妇孺皆喜。
在我年少的记忆里,夏天一到,家家户户晌午都吃蒜面条,有豆面条、红薯面条、小麦面条等多种类型。特别是“三夏”大忙,人们起早贪黑,抢收抢种,挥汗如雨,晌午回到家,最想吃的就是一碗凉水拔过的蒜面条。你要是这个时间从街上走过,会看见大人孩子都端着一碗蒜面条,三五成群,甚至更多的人聚在一起,蹲在路边的树荫下,一边大快朵颐,一边谈天说地。
在那个年代,无所谓约定俗成,蒜面条几乎都是中原农村人家的晌午饭。吃到了秋、吃到了冬、吃到了春,一年四季都在吃。只不过冬天吃的时候要把拔面的凉水换成热水。如果远方的客人到此,闻到亲戚朋友喷涌而出的大蒜味儿,也大可不必惊讶,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蒜面条好吃,但面条难擀。这是因为,擀面条不仅是技术活,还是个费劲的力气活。在炎热的夏天,一家几口人吃的面条,从和面、饧面、擀面,到切成面条,没有半个小时可不中。为了一家人吃好饭、吃好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,擀面人往往累得满头大汗,肩头搭的毛巾是擦了又擦。以前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,好多家吃的是黑不溜秋的红薯面条。红薯面条更难擀了,因为红薯面黏合度不高,需要反复用力擀压,一遍又一遍,遍数越多面条越筋道。如果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,还会擀成包皮面条。这包皮面条可有讲究了,它不是简单的把红薯面与白面揉在一起,而是各揉各的,揉成面皮后将二者叠放在一块,再用擀面杖擀压使其粘牢。这样做的面条,下到锅里,捞进碗里,黑里透着白,甜中夹着香,看起来开胃,吃起来顺滑。纯白面条(好面条)可是难得一见,如果谁家偶尔做了一顿,这家老少就会端着碗,在左邻右舍跟前炫耀一番后,才依依不舍地送进嘴里,美在心里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,红薯面条才逐渐离开人们的视线。
吃蒜面条,蒜汁儿是必不可少的调料。那个时候搉的蒜汁儿也很简单。在老家,不少人家房前屋后种有香椿树、石香(也叫麝香)菜,每次吃蒜面条,都会去摘一些放进蒜臼里,与青辣椒、蒜瓣、盐斗(盐巴)一起搉碎,气味芬芳,沁人心脾。面条锅里下的青菜,主要是在地里薅的野菜,像马齿苋、灰灰菜、面条菜、玉米菜、扫帚苗、狗儿秧等,也有生产队里种的红薯叶、萝卜苗、白菜苗等等。天将午,饥肠响如鼓。一家人静等开吃。待到面条甫一出锅,便捞到凉水盆里拔一下,再捞到碗里浇上蒜汁儿,胡乱搅拌几下,就急忙往嘴里扒拉。当时的蒜面条就像美味一般,感觉是那么的好吃,再吃也吃不俗,再吃也吃不够。后来才知道,蒜面条不仅能填饱肚子,而且还能防病治病,按照现在的说法,属于食疗的一种。比如说,要是有人拉肚子了,就赶紧用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,做一碗不放盐的蒜面条,多放两瓣蒜搉碎浇上,再拿个碗扣上闷一会儿,吃完之后就好了。恰似灵丹妙药,每每灵验之极。
在乡里工作那两年,二十出头的我也和老同志一样,每天骑着自行车往村里跑。有时遇到中心工作任务重,晌午赶不回去吃饭,就留在村干部家吃蒜面条。只是辛苦了村干部家的女主人,大热天里,一擀就是满满一锅簰。在小院里的绿荫下,吃着可口的蒜面条,讨论着未了的工作,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有时邻居也端着碗进来,随便找个凳子坐下,边吃边聊。那种温馨和谐的吃饭场景,几十年后仍然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有时候我就在想,如果现在的领导干部下乡还吃蒜面条,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?
离开了家乡二十多年了,我依旧忘不了蒜面条。其中包含更多的是对家乡的思念,对故土的依恋,对往事的回忆。懂我心思的老伴,只要没有特殊情况,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,十天半月总要做一顿蒜面条。只是城市里没有香椿树,更没有石香菜,蒜面条少了些许家乡的味道。
今年清明节回老家上坟,顺道去看望年已古稀的大姐,外甥媳妇问晌午吃啥饭,我不假思索的回答,蒜面条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,蒜面条的做法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你看,辣椒不再与蒜汁儿混在一起,而是放在油锅里炒一炒,待放焦了以后再搉碎。调和好的蒜汁儿碗里,还倒进了小磨香油和香醋,油花在表面四散漂浮,碎蒜在中间沉沉伏伏,看上去碧绿金黄,闻起来酸香扑鼻。锅里下的青菜,是从市场上买回的菠菜和韭菜。早春的菠菜红根绿叶,头茬韭菜有助于提升阳气,极富营养。眼下的日子比过去好了许多,人们还喜欢吃蒜面条吗?我随口问道。都在吃,就连小孩子们也喜欢吃,很多人家还用上了轧面条机。外甥还告诉我,镇上还开了几家专门做蒜面条的小吃店,中午都是顾客盈门。看来,蒜面条的魅力经久不衰,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,绵延不尽。我顿时觉得,蒜面条不仅只是一种饭食,更是一种文化,吃一碗蒜面条,就是一次文化的传承。 (作者:朱硕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