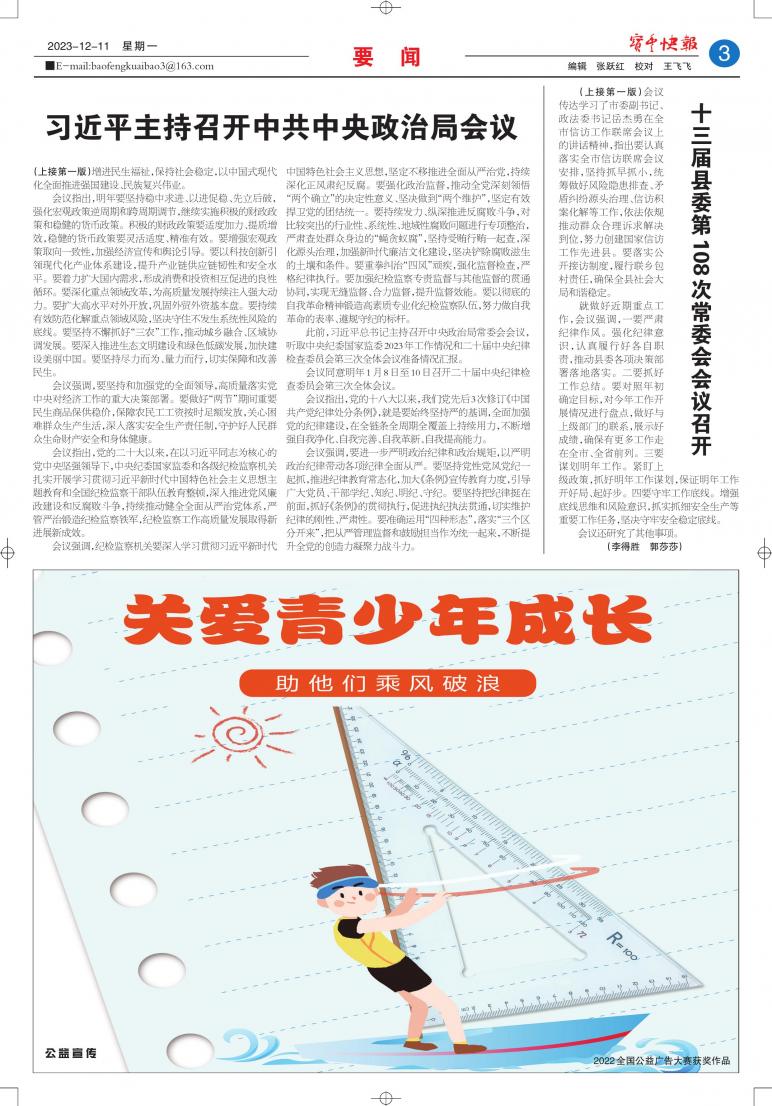第四版:文艺·副刊
老街豆腐坊,是我家六叔开的,在三里五村很出名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六叔出村卖豆腐,只要进邻村吆喝几声“割——豆腐”,一会儿就会被抢光。
六叔家临着大街,坐北朝南,门前有棵大榆树。豆腐坊位于他家的两间西厢房里,门口左侧垒着一个石台,石台上安放着一块边沿高约4厘米、宽约3厘米的长方形凹槽形青石板。青石板前开凿了一个宽约4厘米的出水口。青石板旁时常摞着几个长方形坯模一样的木模具,模具长约100厘米、宽约45厘米,四周竖立的木板厚约0.8厘米、高约10厘米。模具旁叠放着几个比模具大点儿的长方形托盘(箅子)。
豆腐坊最南边支着一盘石磨,磨盘上空吊着一个灰色瓦罐,瓦罐下凿了一个小眼,小眼上扎着一根黄豆般粗细的小水管。石磨西北不远处挂着一个吊单(十字架的木棍四个端点绑着一块稀布的四个角),吊单下放着一口锅。吊单北面是灶台,灶台上支着一口大锅,锅台边放着一口缸。
磨豆腐。六叔把泡好的黄豆搲到磨扇中间,堆成一个尖锥形,套上小毛驴,用一块布蒙着眼睛,给驴戴上笼嘴,把瓦罐加满水。紧接着,六叔把瓦罐的水塞打开,驱赶小毛驴。随着磨扇吱吱扭扭地转动,一粒粒黄豆便滚进磨眼,豆汁顺着两个磨扇中间的罅隙,欢快地流进磨盘上开凿的环形凹槽里,渐渐汇成一条乳白色的小溪,从凹槽出口流到下面接豆汁的桶里。
其间,六叔不仅要用小炊帚把黄豆不断往中间拢,防止石磨空转,还要不停往扇磨上和瓦罐里添豆、加水。看着磨盘周围小毛驴坚实的蹄印,我便会想起“磨道里寻驴蹄——啥时也现成”的歇后语。
滤豆汁。桶里的豆汁注满了,六叔就把豆汁倒进吊单里。六婶在一旁有节奏地晃着吊单,豆汁哗哗流进了下面的锅里。待豆汁过滤好,六婶把吊单往上一抖,豆渣便跳进锅旁的箩筐里。晃吊单的整个过程就像表演舞蹈,煞是好看。
熬豆汁。把过滤后的豆汁舀进灶台上的锅里进行熬制。熬制时,灶台下火苗呼呼舔着锅底,锅里的豆汁细浪翻腾。熬了大约20分钟,豆汁便熬成了“稀里糊涂”的豆浆(豆花)。
点豆腐。点豆腐前,六叔把锅里的豆浆舀到缸里,左手端着装有调配好石膏水(卤水)的盆,将石膏水缓缓倒入豆浆里,右手握着一个另一头带着小木板的木棒向上抖。倒一点儿石膏水,用木棒向上抖一下,并仔细观察翻起来的豆浆的色相。如此三番,直至恰到好处,才停止加卤水和搅动。少顷,缸里的豆浆就分离成了上面漂着清水、下面是块状物的豆腐脑。这就是“卤水点豆腐——一物降一物”的由来。
压豆腐。用舀子把缸里上面的清水撇出来,把木模具放到箅子上,在箅子里罩一张稀白布。然后,把豆腐脑注入模具里,待添加到约8厘米高时,用这块稀白布把豆腐脑包起来,在豆腐脑上放一块比模具略小的长方形木板,再往木板上压一块石头,豆腐脑中的水就被压出来,流进下面的桶里。二三十分钟后,豆腐脑中的水完全被挤压出来时,把石头搬开,模具去掉,揭开稀布,一块四四方方、白白嫩嫩、冒着热气的豆腐便呈现在眼前。
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。热豆腐吃着烫嘴,烧喉咙,要晾一会儿才适口。这句话提醒人们无论是办啥事,都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,不能操之过急。
现在,老街豆腐坊像六叔一样渐渐隐去身影,他的儿子在城里开了一个现代化豆腐坊,但老街豆腐留下的传统手工艺,留下的纯正地道的豆腐气味,仍让我觉得余味无穷,不能忘怀。